

文、圖/廖博思
在廣東潮汕和閩南等地,清末以來出海謀生的番客(海外華人華僑)通過民間銀信局或批局匯寄至國內的匯款及家書,被稱作“僑批”(潮汕話中“批”即“信”)。而在經歷了數十天顛簸航程,歷盡千辛萬苦僥幸登岸后,番客們寄出的第一封報平安的批,便是“平安批”。
《平安批》是陳繼明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作品圍繞主人公鄭夢梅展開敘述。鄭夢梅在年屆中年時,為了重振家業,決定獨身前往南洋謀求發展。在暹羅,由于他識文斷字,他成為了一名寫批師傅,誤打誤撞接觸了僑批業,并從此將經營批局作為終生事業。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潮汕的僑商們紛紛采取各種措施來抵抗日本侵略者,并積極救助戰爭中的無辜平民。當海上的郵路被封鎖時,鄭夢梅與其子乃誠展現了深厚的愛國情懷和責任感,他們毫不猶豫地投身于救國大業中。他們化身水客(即負責送批的人),冒著生命危險走陸路送番批,開辟新郵路代替海上郵路,在戰火中保持了一條運送番批及抗戰物資、捐款的生命線……全書篇幅不長,但細細讀來,讓人血脈僨張、
小說里,鄭夢梅的一生幾乎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小說通過他在個人事業、家族榮譽、行業操守,以及民族尊嚴等諸多層面的堅守與抉擇,以令人感念的具體事件與敘事細節,深刻詮釋了“僑批”人胸懷天下的家國情懷。有意思的是,對華僑文化稍有了解的讀者,透過鄭夢梅的形象,能聯想到許多心懷大義的華僑形象,他們既有華人浸在骨肉中的勤勞、奮進,又有海外游子割舍不掉的對家國的孺慕之情。
“平安批”作為本書的名字,既是串聯起整個故事的線索,也是故事的名字。依照小說中董姑娘的說法,所謂的“平安批”,又被稱為“番批”。“番”是指在外國的或外族的男人給國內家人或親人等郵寄的信件,稱為“番批”。“番批”為什么又被稱為“平安批”呢?在書里,作者是這樣寫的:“從小就知道有一種家書叫‘平安批’,人也因此分為兩種,一種是寄平安批的人,一種是等平安批的人。”說簡單點,家人天各一方,長期不能相見,來回的“番批”最主要的內容就是互報平安。“平安”二字的意味,幾句話很難概括,如同書里寫的那樣:“從小就知道有一種家書,叫‘平安批’,在少年阿佛的想象中,人因此而分為兩種,一種是寄平安批的人,一種是等平安批的人。后者比前者可憐多了,除了在家里苦等和拜老爺,什么事也做不了。收到一封平安批,心里的石頭就落地了,至于以后,暫時可以不牽掛了。而前者,就算受盡磨難、吉兇未卜、生死難料,總少不了一種逍遙自在、獨來獨往的味道。對那些過番者的想象,在一個不識愁滋味的孥仔心里,像做夢一樣無邊無沿。那是一個無限大無限遠的美好世界,那個世界名叫番畔,要多大有多大,要多遠有多遠,要多美有多美。”——正因為如此,陳繼明方才會飽含深情地把“平安批”用為小說的標題。
作為小說文本,《平安批》的結構不算復雜,甚至可以稱為平白——總體為集散式結構,整體依循線性時間順序組織敘述,閱讀起來并不吃力,但卻讓人感覺十分精巧,文中設置了幾組不同的雙面結構:溪前與溪后、老祖與兒孫、番客與潮汕姿娘、僑商與南洋勞工、傳教士與信徒、侵略者與死士、中國人與外國人……這些共同構建了一個立體的,真實的故事舞臺。
在書中,我個人很喜歡的除了以主角鄭夢梅為首的潮汕僑商群體的發家史之外,還有書中彌漫著的一種氤氳的神秘感,無論是小說開篇展現的廢井傳說、十三少和九爺的喃喃自語、阿嫲如在霧氣中隱隱約約的“梅仔”、“阿佛”的呼喚、一些微妙細小的氣味,再到鄭夢梅的出門遠行……這種敘事風格與一般對個人奮斗史的正面描寫是不同的,它并不直給,相反,《平安批》對鄭夢梅的多數描述都如同泡在水中的紙條,又或是隱在潮濕的水霧中般樹影枝條,影影綽綽,又讓人品出一絲命運的既定。當然,故事中還融入了一些諸如家族詛咒的懸疑感:家中長輩的陸續死亡、神秘的預言……不過,這些在故事的后面來了一個很絕的揭露,為了保障閱讀體驗,我就不劇透了。總的來說,《平安批》可以稱得上是我最近讀的嚴肅文學中,最為反套路的一本。
書中的故事值得玩味,書外的故事同樣有趣。作者陳繼明出生于甘肅省甘谷縣,曾經長期在西北工作生活,后遷居珠海。為了創作《平安批》,他在汕頭駐地一年,查閱資料、整理番批、走訪當地老人,扎實的案頭工作醞釀出一個既“潮汕”又不“潮汕”的故事。
總的來說,《平安批》不失為一個管中窺豹,了解潮汕僑商文化以及僑批文化歷史的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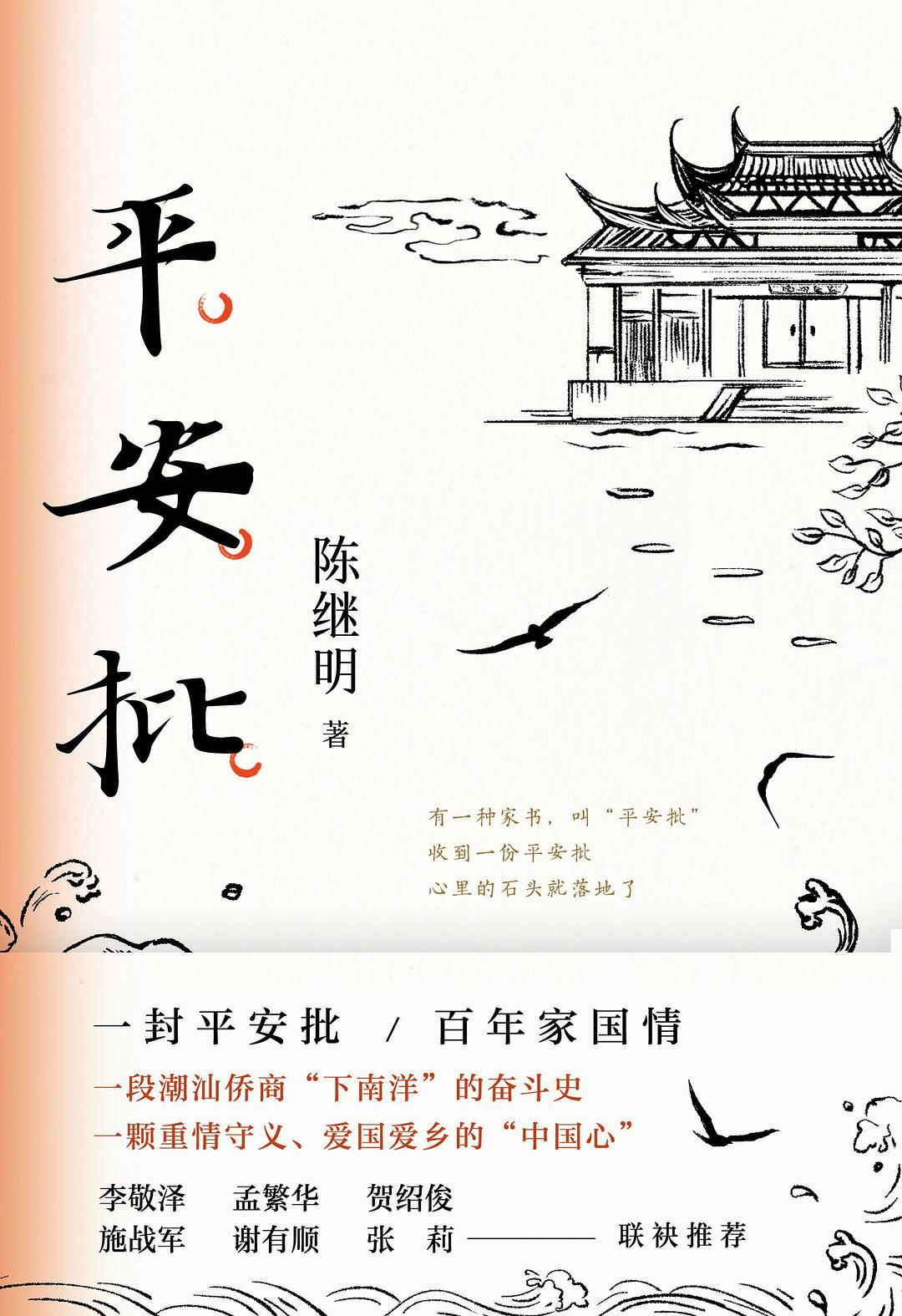
《平安批》
 繼續訪問
繼續訪問